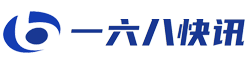19世纪末以前,库尔德思想中几乎没有把库尔德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情况。唯一的例外可能是17世纪的哲学家艾哈迈德·哈尼(Ahmad-i Khani)。几乎成为学界共识的一点是,“库尔德人”——20世纪上半叶在某些英国档案中一些由“部落首领”(tribesman)统率的人群,或“某个几乎不与外界接触的部落”——二百余年的确来代表着一个可辨识的群体,不过同样明确的一点是,族群意识在库尔德人当中的萌发,最多也就能追溯个一百来年而已,这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类似。这一认同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身份和宗教共同体成员身份的理念,其结果则并未产生清晰可辨的“政治忠诚”。 库尔德人跨国认同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库尔德人——与该地区其它许多族群类似——直到最近才认定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呢?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译注)对此给出了一个间接答案,侧重分析“民族的雏形”,所谓雏形是指一系列根本性的、长期存在着的认同符号,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存在对之进行怀疑批判的必要。梅隆·本文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推进了这一论述,指出“身份认定的整个游戏反映出移民之间缺乏联系。本地人则从不追问其认同问题。” 在本地人当中,五花八门的认同(涉及宗教、本土、跨国性、土地、家庭等多个维度)基本上和谐共处,并无多少冲突。认同之间既有一定清晰性,又呈现出交叠状态。中东地区的语境有一与他人迥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如巴内特(Barnett)和特拉米(Telhami)所言的,“国家认同具有一种跨国的性质。”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库尔德人社群的流动还是有其族群意识作为核心支撑,而非离散割裂。不过这一考虑,可能没揭示出事情的全部面貌。例如,它没法解释该地区早些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流动性与多面性,或者难以解释为何1920年时欧洲帝国主义者想要在色佛尔条约中(Treaty of Sevres,欧洲国家于1920年签订的瓜分一战中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条约——译注)成立一个库尔德政权,但库尔德人却和当时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原文是“阿塔图克”Ataturk,土耳其文“土耳其之父”,凯末尔革命成功后获颁此称号——译注)站在一边抵制这个条约。后者提示着这样的事实——按尼古拉斯·丹佛(Nicholas Danforth)的说法:“政治忠诚能够并且的确超越了民族认同,其方式对如今的我们而言并不难理解。” 超越自决的表面修辞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半自治区拟定于9月25日单方面举行全民公投,围绕这件事情的争论,基本跟上文提到的各种理论上的考虑关系不大。坦白讲,和历史类似,这次全民公投也跟库尔德人对自身处境的抱怨关系不大,它更主要地涉及到地缘政治的博弈。 此次公投希望能够重建位于巴格达的中央政府与(边缘化、且经常受到压迫的)高度分化的库尔德共同体之间的权力均势。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力挺公投的人大多想要藉此占据那些不属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之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区域包括基尔库克省(Kirkuk)——一个族群成分混杂的地区,但拥有伊拉克境内原油储量的40%——以及尼尼微平原(Nineveh Plain),许多基督徒在那里定居。这些基督徒与伊拉克境内许多其它少数群体一样,如今仍处于库尔德军事力量的攻击与暴力威胁之下,其手法“使人联想起库尔德人曾经对自己同胞使用过的那些镇压手段”。 以色列的暧昧上述这些因素加强了中东内外诸多势力对此次公投的广泛反对态度。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态度最鲜明,土耳其和伊朗也紧随其后:这一“库尔德人的小伎俩”(Kurdish gambit)为最近的土耳其-伊朗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一风潮中唯有以色列是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外。如其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所言,他的国家“支持库尔德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正当努力”。不过,这对那种理想主义的宣示无甚帮助。要不然巴勒斯坦人追求建立自己国家的诉求就会得到同样的对待了:然而他们的命运和伊拉克库尔德人截然相反,已在外军的控制下生活了50余年。 伊拉克北部约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都要透过土耳其临近地中海的港口杰伊汉(Ceyhan)输往以色列。《金融时报》的一篇报告称,2015年5月至8月间,以色列大约有77%的原油需求都要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口。基于此,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军事、能源及通讯相关的工程项目大多都有来自以色列的资金援助。最后,以色列(这方面,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并无不同)视此次公投为一种抑制伊拉克(现有的以及潜在的)战略及经济力量的工具。 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何库尔德人——自从60年代以来它就一直在军事、情报及商业合作方面得到以色列的鼎力援助——被多方视为是自身与阿拉伯方面的敌手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战略资产。 伊拉克的利益1988年的安法尔(Anfal)大屠杀——其背景是两伊战争——以组织有序的方式夺去了七、八万名库尔德男女老少的性命,如今仍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以及其它人心目中的一道巨大创伤。这场严重的暴行究其起因乃是源自于萨达姆·侯赛因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1983年7月23日,库尔德人曾协助伊朗军队攻占某伊拉克小城)。 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一悲剧性的过去并未准确反映出伊拉克历史及其各族人民的多重面向。此处提及一下现任伊拉克总理、同时也是什叶派成员的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如今在逊尼派阿拉伯人口中享有的高支持率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1921-1958年间伊拉克共有23位总理,其中12位是逊尼派阿拉伯人,4位是什叶派阿拉伯人,4位是逊尼派库尔德人,另有2位为基督徒,1位为逊尼派土耳其人。 同样值得一谈的是,巴格达仍容有百万名库尔德人定居,且未受族群或派系暴力的困扰。巴士拉(Basra)的主体人口是逊尼派。萨马拉(Samarra)的逊尼派占主流,但保有两座重要的什叶派遗迹。 公投的支持者希望能将萨拉丁省(Salah ad-Din)和迪亚拉省(Diyala)纳入新的库尔德国家版图,这两个省份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反映着伊拉克的多元性,将其中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分裂出去,只会催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和种族清洗。况且库尔德人内部的多样性也并没有少到哪里去,它与其它中东国家的人口结构类似,也处于宗教(包括逊尼派及什叶派)、族群与派系等各种认同的犬牙交错之中。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要诉诸一种非派系性或是非族群的民族主义来观照该地区的历史与当下,一幅类似于前南斯拉夫(1999)的未来蓝图——在那里透过追求族群纯洁性的方式来运用(以及误用)民族自决原则的做法,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大屠杀——这并非完全不现实的,在维持其原先所具备的包容性的同时,也要因地制宜地照顾一下特殊性。 这次公投与之相反——它谈不上能够成为“区域稳定的支撑点”——欠缺包容性方面的考虑,并且诉诸了一种早已过时的理论来支持分离,将塑造语言、族群或宗教的同质性列为正当的解决方案。它的通过和执行,对伊拉克人民而言可能意味着一场新的大灾难,其后果或与1922-1923年间希腊与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订的条约类似:身份认同的种族化以及围绕族群和派系来构建身份认同的做法,将首次在这一地区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性。 这一现象进一步证明了以下论断,这一点在如今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伊拉克人一方面需要继续关注国家的重建,另一方面也要以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去找到回归历史的路径,设法发掘出千年以来一直贯穿于传统的伊拉克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通情达理的、包容特殊性的氛围,使古老而繁荣的“伊拉克地区”重新焕发生机。 (翻译:林达) |
热门关键词: